
 立即打开
立即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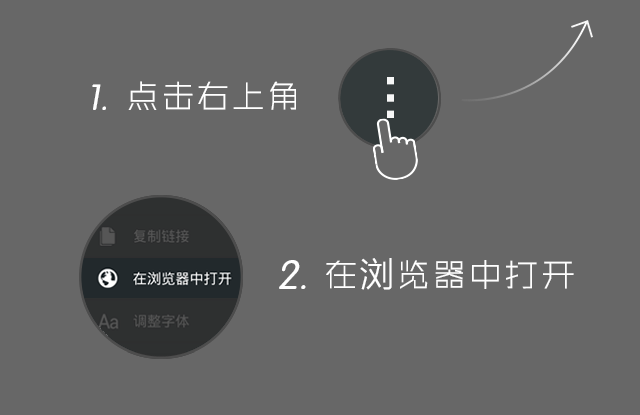
中国新闻周刊 2017-05-02 19:49:45
核心提示:原标题:三里屯洋妞,gay吧,和无处安放的夜红色跑车掠过工体北路,一头扎进滚滚雾霾,丢下阵阵引擎咆哮的轰鸣。车轮轧进工体西路,一排大腿根雪白的姑娘映入眼帘,这群全北京睡得最晚的人玩儿得正嗨。这里是三里
原标题:三里屯洋妞,gay吧,和无处安放的夜
红色跑车掠过工体北路,一头扎进滚滚雾霾,丢下阵阵引擎咆哮的轰鸣。
车轮轧进工体西路,一排大腿根雪白的姑娘映入眼帘,这群全北京睡得最晚的人玩儿得正嗨。
这里是三里屯西的酒吧群。
魔宙说,这里是全北京夜生活最丰富的地方,中国性解放的先驱之地。
有钱有颜的人在这里找到天堂,无钱无颜的人在这里仰望天堂。
五一的夜晚,我站在工体北路的天桥上,看着不时飙过的豪车,开始了奇幻的三里一夜。
白皮指南
指针向北,夜里十二点,我来到三里屯太古里南区的酒吧街。
同行的Chanking开始吹嘘他的独门秘籍《三里屯白皮指南》,作为一位90后北京伪土著,他自称通晓五国语言,留学东西洋,前女友遍布五大洲。
进到常去的酒吧,两杯马尿whiskey上桌,我们在离吧台和门口不远处坐下来。
Chanking看着靠窗的两位外国女人说,“她俩没在等人,我们过去吧”。
常规搭讪,相互介绍,来自美国的Sarah和Ciel和我们攀谈起来。
聊了几个套路回合,我的英语不够用了,而这时的Chanking才刚刚开始谈笑风生。
他的舌头好像会打转,一会儿用波士顿腔调侃Mary Jane,一会儿用纽约土语背金斯堡的《嚎叫》,一会儿切换到南方口音聊中国饮食和剥皮蛋。
四个人你来我往,相谈甚欢,我瞅准时机,提议去跳舞。
我和Ciel进了舞池, Chanking则和Sarah挽在一起。
看着人高马大却灵巧异常的Ciel,我有点尴尬地表示自己舞技笨拙动作僵硬,Ciel大方地说她来教我。
就这样,我在一个31岁的美国女人(后来才知道她的年龄)的指引下,开始了探索人类灵活身材的曼妙之旅。
期间我发现Chanking和Sarah不见了,并未在意。
稍后俩人回到座位的时候,我和Ciel也从拥挤的舞池脱身。
热聊继续,酒水不断。在互加了微信和脸书之后,我们友好告别。
我好奇,Chanking怎么会就这样离开?后来才知道,在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和Sarah去了趟洗手间。
三里屯70秒视频火了后,单纯的我曾研究过每一帧画面,最后得出结论——这只是无良营销者用手机录制的低劣音像宣传。

然而Chanking向我证明,卫生间比试衣间时间更长久。
出了酒吧,三里屯的晚风让我打了个冷颤。
路边有两个外国人不时用流利的普通话对来往美女说“飞吗?”、“飞吗?”。
Chanking有点文不对题地来了句:
午夜捡尸
时针偏东北,凌晨两点,我们来到工体。Chanking说今晚如果运气好,他要捡回尸。
所谓“捡尸”,就是把喝醉的女生带走,Just do it。
看着一排望不到头的车停在路边,我正要感慨有一半的车愣是叫不出名字,Chanking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如果只是来捡尸的话,最好不要开自己的车来。一是留下了监控的车牌号就是留下麻烦;二是女人一喝多就喜欢往你的车里吐,那味儿怎么都洗不掉,嗨,别提多扫兴了。”
他倒是对车没什么兴趣,只是专注于辨认路边的美女是否喝茫。
从工体北门转到工体西门,近半个小时的路程。夜色下,我们和“猎物”玩儿着躲猫猫。
正盘算着进酒吧里主动“灌尸”时,路边蹲着的女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光腿、长发,Chanking凑上去试探,女人似乎还算清醒。
我被之前的碰壁扫了兴致,只是站在不远处等着Chanking失败,谁知Chanking居然和她聊了起来。
“你状态很不好,怎么喝这么多?”
“心情不好。”
“没事儿,谁都有这个时候,我扶你走吧。”
“好。”
Chanking的一只手,此时已经搭在她的背上,两人似乎聊得还挺欢快。
我很尴尬地保持了一小段距离跟着他们后面走,默默计算着他们直奔对方灵魂还要多少时间。
10分钟。
只过了10分钟,Chanking就转过头告诉我他正在叫快车,“要不要一起?”
我对着他遥遥挥手,祝他保重身体。
Chanking嘴角漏出邪魅的笑,同样朝我挥了挥手,扶着他的“战利品”走向黑夜的另一边。
Gay吧激情
指针正东,凌晨三点,我只身一人来到了号称亚洲最大gay吧的Destination(目的地)。
点酒时,邻座微胖的男士向我搭讪:“一看你的脸,就知道是第一次来——长得好看的都在前半夜。”
(??)我黑人问号,“长得丑是原罪?”
索性顺着话题聊开,假装虚心求教,询问新手指南。
他告诉我,二楼是储物间,一楼东侧是舞池,走廊房间门口贴着的“熊”、“猴”表示不同的主题房间——“熊”指壮的,“猴”指瘦的,还有“猪”是指胖的。
我调侃他介于“熊”和“猪”之间,他未置可否,邀我去舞池看看。

酒壮怂人胆,我闷了两口酒,假装酒劲上脑,牵起了他的手。
一开始,彼此还算克制,只是牵手摇曳;随着舞池地板的震动和音乐节奏的带起,他开始了进一步动作——
先是不停地拍打我的臀部,接着用不可描述的部位蹭我,然后试图亲吻。
我赶紧道歉陪笑,表示玩不起,闪出了舞池。
这一场算是热身,之后的我胆子更大了一些。
在舞池边我又认识了一位身高1米6左右、穿红色格子衫浅色牛仔裤的少年。
我夸他五官清秀,眉宇间散发着温雅气息。
他告诉我他是戏剧专业的学生,趁着来北京参加演出,抽空泡吧。
“你不仅长得好看,声音也很好听,叫起来感觉肯定棒,”我继续恭维,或者说,试探。
他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调皮的说:
直男如我,深知男人的话都是骗人的。
但是当我面对这么一位“夭夭桃李花,灼灼有光辉”的粉面小生的吴侬细语时,竟毫无抵抗地选择了相信。
我们挽手跨进舞池,在劲爆的音乐里开始了互相碰撞。
透过厚厚的粉底,我观察着他精致的五官和欲语还休的眼神。频闪灯打过他脸上的那一瞬,恍惚间看到了《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
那细腻分明的唇角,竟有种等我吻他的错觉。
该来的总不会来,舞过三巡,我们点到即止——自然地松开微汗的手,自然地分道扬镳,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酒吧即将打烊,我踱步出门,结束了这暧昧微妙的一夜。
写在最后
指针正南,凌晨六点,我坐上了回程的地铁。
从黑夜撞进黎明,由地下转入地上,有些恍惚。
路过卖煎饼果子的早点摊,我停下来。大妈看我一身酒气,撇了撇嘴:“年轻人没事少喝点酒,多看看佛教的《心经》,很有用的。”
我没接话,把胸口挂着的十字架往衣服里塞了塞——为搭讪洋妞而戴,此时显得不合时宜。
嚼着煎饼果子,看着凌晨六点依然华丽如烟的京城,我想起大学时读的《爱默生选集》——“紧跟变革,总有一个放荡淫乱的时代。”
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如我辈,究竟是放荡淫乱,还是灵魂无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