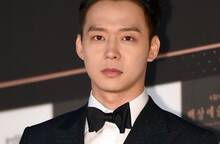金克木:《论语》中的马
- T大
《论语》中的马
文 | 金克木
科学,技术,是一?是二?
自然,人事,孰重?孰轻?
忽然想到了马。
马有过辉煌时代。马曾经在亚洲东西南北纵横驰骤。印度的最古文献“吠陀”中歌颂马。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最大祭祀是“马祭”,由王族武士举行。中国史书称赞中亚大宛的名马。在台湾大学创建考古人类学系的李济教授说过,不仅有丝绸之路,还有彩陶之路。我想应该还有横贯亚洲的名副其实的上古“马路”。
驯服野马很不容易。马一旦为人所用便显示出威力。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中亚许多古代民族无不凭藉马而辉煌一时。更古些时,在中国黄河流域,马的发挥作用是拉车,特别是战车。车上一个御者指挥马,一个射者弯弓搭箭远射,胜过手持兵器的任何步行人。至今秦始皇墓的大队兵马俑还在地下排列成仪仗队,显示两千多年前的无比威风。
马的特长在于其力度和速度。发现这一点不难。驯服野马为人所用就不容易。认识力度、速度以及效率的意义而加以推广,那就是文化思想的发展,不是任何人、民族、国家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了。把马作为交通工具也是发挥马的作用。但若只供贵族官僚摆架子显身份,不能广为平民百姓所用,那就是把马当作装饰品了。马不是文化。用马和识马是文化。认识马的意义是文化思想。闪电的迅速,古人早已见到。但直到富兰克林做实验才把天上的电引到地上,然后才为人所用。无线电、原子能,无不如此。可以用来加强人的能力,也可以用来杀害人,进行大破坏。关键在人。人的事才是文化。
科学只认识世界。无论发现什么定律都不能直接变动世界的一丝一毫。科学化为人的技术,才能改造世界。怎么改造?是加强还是破坏?技术也管不着。那是在于人。要在人的社会文化思想发展变化里找答复。不分别科学和技术,再把人做的事的责任和原因归咎于科学认识和技术发明,这是思想不清晰,会引起一些不能答复也不必答复的问题。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相通而又必须先分别。

古代壁画中的马
“白马非马”不是我们的两千几百年前的老前辈就知道了吗?发挥了什么实际作用?庄子观察到了浮力现象。阿基米德也发现了浮力。两人的想法,或者说思维的线路,大不相同。船和航运的发展不是他们的功劳,那是技术。
不妨看看《论语》这部古书里的孔子怎么认识马和看待马的。
东周“春秋”正是马车的辉煌时代。《论语》里是用“千乘之国”表示富强的诸侯国家的。那就是有上千辆的车子。每车用四匹马驾驶,称为“驷”。“百乘之家”那就是次诸侯一等的大夫的属地,称为“家”,不称为国。至于“万乘之国”,那是到战国的《孟子》里才有。《老了》里出现过一次。“乘”,马车,战车,是富和强的标志,好比几十年前讲钢产量。《论语》中讲这些“乘”以及“大车”、“小车”、“兵车”、“御”车的不算,“司马牛”、“巫马期”是人名,也不算,此外提到“马”的有八处,试检查一下。
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这是把马当作牲畜,和狗一样。
二、“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
这里说的是作为家产的马车。放弃了,自己出国。
三、“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
四、“乘肥马,衣轻裘。”
这都仍是作为用品,产业。
五、“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这个故事,《左传》里有。《公羊传》、《穀梁传》里没有。打败了往回跑。跑在后面的叫作“殿”,即“断后”,保护本军,挡住追军,是立了一功。这位孟之反自己说不是立功,是马跑不快,打了马一鞭子。这一次齐鲁之战,孔子的学生冉求、樊迟都参加了。孔子称赞败将有道德,“不伐”,不夸耀自己,不吹牛。实际上,马是冤枉的。孟之反是说假话。这里的驾战车的马是作战工具。
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是别人记孔子言行的话。马棚起火烧了。孔子上朝回来,问人有没有受伤的,不问马。朱熹的注说,孔子不是不爱马,但更看重人,来不及问马。又说是:“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这里还是把马当作家畜、家产看待。孔子上朝、退朝必定乘车,因为他说过,做官当大夫的“不可徒行”,自己不能徒步走路。看来他上朝、退朝的驾车的马不在马棚里,安然无恙。厩里不知还有几匹马。伤了,跑了,当然没有人重要。
七、“有马者借人乘之。”
这还是认马为家产,工具。“借人”是借给别人。

秦始皇兵马俑中的战车铜俑
八、“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这里的马仍是作为家产。“千驷”照说有四千匹马,就算是夸大,实际上也不会少。然而无德,所以无名可称。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淄出土的殉马坑里有几百具排列整齐的马尸骨,据说就是齐景公墓,可见这里说的是事实。但这里有问题。有“千驷”就是“千乘之国”。马大批殉葬,战车谁拉,岂不要报废?齐景公死了,继承人怎么肯做这种伤损国力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孔子讲的是“驷”,不是“乘”,可见这些马不是战马,大概是宠物。所以王爷一死,后人就不肯花费草料养只供观赏的废物了。
《论语》里孔子讲到马,没有一处注意到马本身,只把它当作一件东西,不提马的特点。这不是要求古人现代化,因为《论语》里还有一处提到马,观点就不一样。
“驷不及舌。”
马快也赶不上舌头动的快!就是说,讲的话比马还快。话讲出去就收不回来,不比马还可以停下回来。这里讲的是速度,讲到点子上了。不过这话不是孔子讲的,是他的学生善于言语的子贡讲的。子贡又善于“货殖”,也就是做生意。孔子还夸他“亿则屡中”。就是说,他不但注意市场信息,而且能够正确预测(亿,臆),还多半测得准(中)。《史记》里记载,子贡不但会做买卖,发财,而且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外交人才。他曾出国一次便影响五个诸侯国的兴亡,真了不起。子贡也是《论语》中注意到自然现象的一位贤人。
“子贡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太阳、月亮是谁也跳跃不过去的。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他说:“君子”犯了错误好像是日食、月食。错的时候人人见到。改正的时候,人人钦仰。他注意到日食、月食的情况,观察自然现象,用来比喻人事。
孔子也说过“譬如北辰”。用天上的北极星比喻人事。他也说过快慢,时间长短。可见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重视,思维方向在人间,在事物对人的用处,不在事物本身。这是技术观点。也可以说是价值观的问题,一切工具化。他说过“欲速则不达”。没指出不达不是速的问题而是速的方法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另一位孔子,和这不同。那是在《孟子》里。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这是孟子引孔子的话,在《公孙丑》章中。这句话提到了信息(“传命”)、传播(“流行”)和设立驿站(“置邮”),像烽火台一样一站一站把信息传下去。这样传播信息很快,但是“德”(包括正面、反面,好的、坏的)传播起来比这“邮传”还要快。这真是非常现代化的思想了。这第二位孔子同发现风力、水力的庄子一样(见《逍遥游》)已经到了科学的边缘上了,可是连什么技术也没有发明,更不用说去发现什么自然界本身的定律了。实在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再举一个马的例,是《周易》的卦爻,更古。
易卦中以乾卦象天。天的象征是龙。六爻爻辞中多处说龙。又以坤卦象地,地的象征是什么?
“乾:元、亨、利、贞。”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原来地的象征是牝马。可是爻辞中没有说马。凭什么牝马即母马能配上地?决不是由于生殖。马一胎只生一个。猪一胎生得多,怎么豕不能配地?我看道理很明显。龙是天上空中最活动的假想生物,是天上活动力量的象征。地上最活动的真实的生物就是马。马成为地上最大活动力量的象征,所以马能配天上的龙。坤卦辞、爻辞说的都是地。方向是“西、南、东、北”。形象是“直、方、大”。这已经到了测量地的几何学的边缘上了。还有爻辞: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天上的龙怎么下到地上来打架了?和谁打架?龙和龙打必在天上,空中。在地上就和马打,比一比谁的力量更大。乾龙属阳。坤马属阴,因此必须说明地是牝马。龙、马都是力的表现和象征,后人便常说“龙马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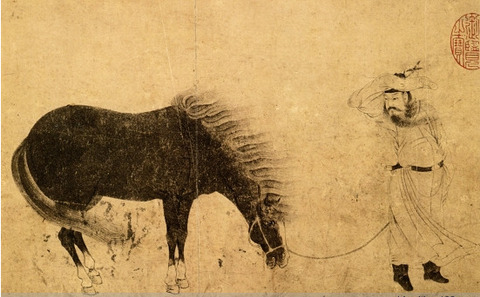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赵孟頫《调良图》
《易》是变易即变化之学,所以将变化归于可知的数,用符号表示。这可能是从甲骨占卜延伸出来的,也可能是独立而相关的思想。这是中国科学思想(认识世界)的开始系统化。这里说的只是卦爻和卦辞、爻辞,不算“十翼”中的发展。那些解说又各有层次,不可混淆,需要先分别。解释乾卦的孔子不是《论语》中的第一位,也不是《孟子》中的第二位,而是《易》解中的第三位。一比较就可见其不同。
想当初,被人驯服了的野马开始大显威力,以类似飞鸟的速度和超过飞鸟的力度到处奔驰,真是所向无敌,如同杜甫说的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马很可能是在西亚、中亚、南亚的平原上驰骤,一直到东亚的黄河流域,在这片广阔大陆上踏出一条又一条“马路”。马出现不久就受到我们先人的赞叹,用来象征大地,配上天上夭矫的神龙。马的远胜过人的惊人速度正像火车、汽车初出现时以及无线电、电子计算机、电脑初发展时一样。然而现象人人见到,道理也人人能知道,化为人能操纵的技术时人人都乐于利用,至于深入钻研其中的规律,那就不是人人时时处处都可以做到的了。这种追求认识自然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少数。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的学说在地中海边也几乎失传千年以上。阿基米德还是死于无知(只知他是敌人)的乱兵之手。
中国人的技术发明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不是第一个发明者,也是第一流的仿造者,而且能使技术艺术化,仿真超过真。但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长于其一,不一定就长于其二。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使用能力的方向路线问题。这里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也不能说是有本末之别。正像科学院和工程院并列一样。我们很早就发明了罗盘。但是磁学是世界上到近代才有的。说孔子的思想不向科学发展,甚至也不重视技术,这一点决不是贬低孔子。何况书中记载的明明有不止一位孔子。
上古的人总是很熟悉男人女人的人的自身,而把自然界看成神秘,力求用占卜等方法去了解自然。到社会发展起来,人事复杂了,这才需要转眼到比自然界更加变化莫测的神秘的社会和人自己。社会结构简单时,人所了解的人自己主要是属于自然界的人的行为。社会复杂化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一群思想家才转过来将社会的人而不是自然的男人女人置于自然界之上。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转变。
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完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线路(不只是方法)。可以明显察觉的一是线性思维,二是对偶思维。这都是从《易》卦爻延伸出来的,而对偶思维在孔子和老子那里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这一点说,岂止几部书中的几个孔子本是一个,连老子和孔子在根本思想上也是一个。作为思想家他们是一类的而且可以说是一致的。这种线性和对偶的思维线路一直传到今天未断,仍旧可以在世界上独放光彩。然而有思想有能力是一回事,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另一回事。这话说得太远了。我已写过一篇《春秋数学:线性思维》。如有可能,想再写一篇《论语数学:对偶思维》。只怕是眼和手已不听使唤,有心无力了。好在这是有心人一望而知的现象,有没有人写出文章倒是无关大体的。(《论语》的四百多章“子曰”中就有四十章完全是对偶体,加上平列的就更多了,还不算包括其他人的“语录”。)
一九九六年
——选自金克木《中国文化老了吗?》,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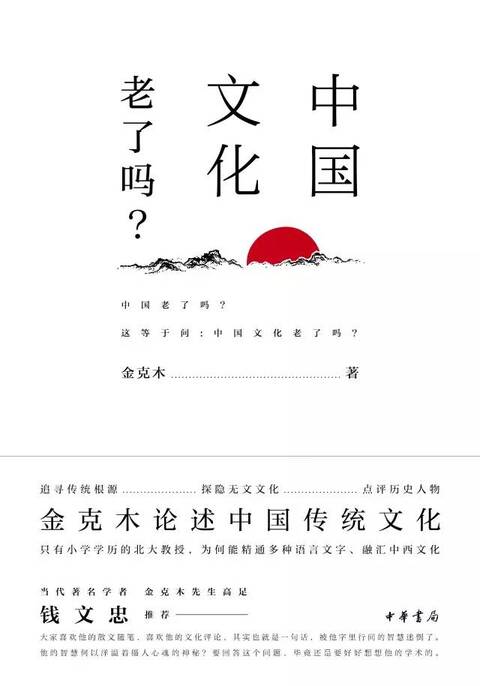
金克木著,《中国文化老了吗?》,中华书局
2016年3月出版,定价48.00元
购买链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