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说》:从“天下大同”到“民族国家”
- T大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面对西方的冲击,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受到严重侵蚀,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和政治方向。梁启超作为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找借鉴。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思想流派均有极大的启发。
张灏先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五四之子”殷海光的学生,承接了五四精神的火种——以民族、国家之命运为终极关怀,又继承了史华慈先生细微而复杂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采取了一种与列文森不同的研究路径,熔思想性和求实精神于一炉,追述梁启超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到新的国家和国民思想之转变,并以此为纽带,从内部探索晚清儒家思想的变化,考察巨变时期的中国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传统逐渐迈向现代。
无论是梁启超在晚清时期的宏观构想,还是张灏在二十年前的国族关怀,直至今日,对绝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在似乎远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危机的当下中国,一方面,世界局势的诸多动荡让我们无所适从,对原本就心存费解的西方普适价值产生了种种怀疑。另一方面,在国内,大众对朴素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缺乏边界的滥用又催生出新的命题。在这个虚无与混乱的时代,我们试图从来自上上一个混乱时代的先贤那里寻找“真问题”,再从来自上一个混乱时代的前辈那里寻求“真解释”。
本文节选自《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六章《新民》之“民族主义和国民理想”小节,感谢三辉图书授权。

张灏
正如我们看到的,1902年梁着手撰写有关道德革新方面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发展他所称的公德。公德的核心仍然是群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他流亡前的改良主义文章中即已占有突出的位置,并且,几乎在1898年他在日本重操杂志活动之后,梁又再次提出群的概念,呼吁海外中国商人组织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重要的问题是,梁现在所谓的群是指什么?首先,作为合群思想的一个重要含义,即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的进一步发展,群指一个近代国家的公民对他的同胞怀有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以及具有组织公民社团的能力。群作为上述意义的一种民德,必然不只对长期形成的、普遍的自私自利表示强烈的厌恶——梁将自私自利看成是传统文化过分强调修身的一个结果,而且直接反对传统社会中盛行的各种形式的原始情感。这些原始情感阻碍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外观似统一,而国中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这些制造分裂的原始情感的盛行,有时甚至使梁怀疑中国是否仍停留在部落社会阶段,而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
不管梁对中国社会分裂的本质和传统文化中缺乏公民团结是如何了解的,在他的文章中找不到像在后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出现的那种情况,即将中国的家庭制度斥为一块妨碍中国社会公民凝聚力的绊脚石。这在梁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核心——“孝”的价值观的态度中十分清楚。梁并没有否认孝是发展新的政治忠诚的一个文化障碍,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固然他有时似乎认为孝可以作为新的群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一个基础。但如果人们注意到梁生活在孝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十分有用的支柱的明治末期的日本这一事实,那么梁的这一态度便不至过于令人惊讶了。
群作为与同胞怀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公民美德,其本身并没有表明它所指的政治共同体的属性。我们必须注意梁在流亡之前的文章中群的概念的矛盾性。在那里,群既指国群,同时也指天下群。现在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梁的群的概念是仍保留了那种矛盾呢,还是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概念?
无疑,1902年当梁撰写《新民说》的时候,群对他来说已明确地是指民族国家思想。但群从一个矛盾的概念转变到明确清晰的国家共同体思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尽管民族国家思想在梁到日本后不久的文章中十分突出,但他并未马上放弃康有为的三世理论,他仍期待未来太平世天下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但是早在1901年,梁就已明确地批评这种天下一统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到他撰写《新民说》时,他猛烈地抨击这种思想阻碍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国家。梁认为,世界主义、大一统和博爱理想在道德上是崇高的,但它们与梁现在所认识的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需的竞争价值观相对立。在这一问题上,天下遭到摈弃,而国家则被奉为忠诚的极点。梁说,人们的忠诚达不到或超越国家这个极点,都是野蛮的象征。在这一问题上,民族国家对梁来说为“最上之团体”。
梁服膺民族国家理想得到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观的支持。在考虑到传统的中国世界秩序观是由儒家士绅设计出来的时候,一般必须区分两个层次。就哲学层次来说,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正如王阳明所说的天下一家。但就政治层次或一般层次来说,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则为中国中心论的意象所支配。在中国中心论的意象中,中国被设想为由无数不同类型的附属国围绕的世界中心。不管这两个层次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大一统的理想,在前者为天下一统,在后者为有等级的一统。
然而,在19世纪,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逐渐被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扩张所摧毁。就天下一统观来说,由于它在儒学中主要被作为哲学上的最高理想,它与政治现实的关系肯定不如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那样密切,因此它仍未受到多大触动。晚清思想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在力图适应因西方扩张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现实中,在一些中国士绅身上出现了一种求助于天下大同哲学观的明显趋向。事实上,康有为的天下大同思想和谭嗣同的仁的世界观就是这种趋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到19世纪末梁成为思想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阻止他承认国家为“最上之团体”的,不是早已被西方扩张击碎的中国中心论的世界观,而是天下大同的道德观。
我们已看到,梁到日本后如何终于逐渐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然而,1902年新民理想形成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思想的出现,它还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观为中国人所久已认识但从未接受的政治现实增添了某种意义和合理性。

梁启超
梁设想的这一新的世界秩序观是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相对立的。首先,他正视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和种族组成的世界。梁指出,整个人类可分成五个不同肤色的种族,即黑色、红色、棕色、黄色和白色人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种族自然是在彼此相互联系中发展的。但他们不是和睦相处,而是经常致力于残忍的种族间的生存竞争。对梁来说,这些种族间的竞争是无可指责的,它们是由世界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人类历史的无情事实。这些竞争的结果,是人种可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变种,即有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前者指那些组织成团结一致的群体,并因而具有在人类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能力的种族;后者是指那些没有结合成团结一致的群体而经常被其他种族征服的种族。在所有的人种中,只有白色和黄色可被称为有历史的人种,而所有其他种族均属非历史的人种。
梁接着强调说,有历史的人种可进一步分为两部分,即有世界史的和非世界史的人种。前者指有能力将他们的统治扩大到疆域之外,并通过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后者显然指那些在人类历史中不能扮演这种角色的民族。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只有白色人种称得上是有世界史的人种。但梁紧接着指出,不是所有的白色人种都能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因为白色人种由三个亚人种组成——“哈密忒人”(Hamitic)、“泌密忒人”(Semitic)和“阿利安人”(Aryan)。
梁认为,虽然哈密忒人和泌密忒人对欧洲古代文明作出过贡献,但近代欧洲文明则是阿利安人独有的创造。历史上,阿利安人由四个民族组成——“拉丁人”、“峨特忒人”、“条顿人”和“斯拉夫人”。并且,梁将近代欧洲看成是由四个民族间的对抗所支配的历史。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的是条顿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是作为最有力的民族出现的。根据对20世纪转折时期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判断,梁进一步评论说,最强大的民族无疑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说,看一下今日的世界地图,人们将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占世界总领土的四分之一以上,统治着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人口,他们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而且,英语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的语言。因此,梁下结论说:“由此观之,则今日世界上最优胜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西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此非吾趋势利之言也,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实如是也。”与传统的世界秩序的意象相反,在梁的世界意象中群体间的冲突是天生具有的,而最终的结果趋向于被条顿民族主宰。
于是,梁思考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是如何变得如此强盛,以致主宰世界的。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当前世界秩序的形成更有关系的,是19世纪末发生的由民族主义到梁所称的民族帝国主义的转变。虽然梁最关心的一直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但直到流亡日本他才深入探讨帝国主义问题。1899年,他写了一篇题为《瓜分危言》的长文。在这篇文章里,虽然他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他的分析以及对其所称的“有形之瓜分”和“无形之瓜分”之间所作的区别,表明他对近代帝国主义具有相当成熟的认识。梁所说的“有形之瓜分”是指领土的征服;他所说的“无形之瓜分”是指权利的割让,尤其是铁路建筑、内河航行等诸如此类的经济权利。“无形之瓜分”显然指的是经济帝国主义。梁认为,“无形之瓜分”的结果要比“有形之瓜分”危害更大。
经济帝国主义思想在以后几年梁发表的文章中愈来愈突出。对19世纪西方工业国家外交政策的详细考察,使梁愈来愈深信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主要是经济的。他评论说,西方在世界扩张的动力根本在于西方18世纪以来发生的惊人的经济发展。这种工业和商业惊人增长的结果导致了西方经济生产的过剩,需要在欧洲之外找到新的市场销路。欧洲列强首先将北美和澳洲作为它们最初的销路,然后转向把南美和非洲作为经济扩张的主要目标。随着这些销路的缩小,西方经济侵略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心逐渐转向亚洲。梁清楚地知道,亚洲一直遭受着西方的经济剥削和殖民掠夺。但在第一阶段,印度是主要的目标。而在第二阶段,梁极为忧虑地评论说,帝国主义的扩张直接指向了中国。虽然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梁认为经济侵略是最基本和最令人可怕的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最可怕的“无形之瓜分”。
与其经济取向密切相联的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民众基础。梁评论说,一个近代西方国家向外扩张时,不只是通过统治者或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操纵,而通常是这个国家所有国民集体努力的结果。它不仅与统治者的政治野心有关,而且与全体人民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梁将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看成是不断增长的国力、举足轻重的经济和国家每个成员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这一意义来说,近代帝国主义与古代的帝国主义迥然不同。“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黩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愤,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过其时而可以息也;今则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呜呼,危矣殆哉,当其冲者,何以御之。”
梁说道,要抵制这种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除了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外,别无他途。正如富有侵略性的西方民族主义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一样,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必须如此。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才能抵抗一个外来民族合力推进的扩张。为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量,必须使它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处在一个危急关头,并因而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梁认为,民族主义的这一普遍特征在国民概念中看得最清楚,国民概念将近代国家与传统形态的国家明确区分开来。正如“国家”术语中的“家”一词所提示的,传统国家本质上分明被设想成一个家庭,即它被看成是某一王朝家庭的私有财产。但根据近代国民概念,国家严格地说是这一国家人民的公有财产。“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概念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与传统统治者的统治权被认为是来自天意不同,近代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的意愿。的确,正如梁所说,在近代西方国家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但重要的是人民既是统治者同时又是被统治者。一个近代公民不仅对政府有应尽的义务,而且在政府的组成和政策的制订中有表达意见和选择的政治权利。
在梁看来,公民权利包括了政治参与。在传统国家中,人民是消极的;与此相反,近代国家的国民则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其组成成员具有共同意志和目的的团体,国家不过是这种民族共同体的一种组织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思想涉及公民权利,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密不可分。梁无疑受了19世纪末欧洲政治思想中一个十分普遍的趋势的影响,这一政治思想将民主和民族主义设想为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这种自然的结合,由于被梁赞美为世界上最强大民族的英国已将它们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而显得更加真实和合理。
总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个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它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一种回应。梁氏民族主义的这种反帝国主义取向需要予以重视,因为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正是这个特点使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始阶段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种明显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和一种公认的政治运动,中国民族主义只有在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才变得具体化起来。但正在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阶段,它分化为两股思潮:一派以梁为代表,将中国民族主义主要看成是迎接外来帝国主义挑战的一个结果;另一派以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派为代表,主要将反满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向。固然,在一些新兴的革命知识分子诸如邹容、陈天华、杨守仁等人的文章中,帝国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这些革命党人是在1902和1903年左右才开始撰写有关帝国主义的文章的,比梁最初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有关帝国主义的观点至少晚两三年。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好几年来一直关心帝国主义问题,但因为与孙中山联系的不断增加——在1905年成立革命团体同盟会时,他们的合作达到了顶点,他们往往将注意力从反帝转向反满。虽然梁从1898年至1903年这段时期有时迁就反满思想,但反满至多是一个次要的和暂时的话题。
从历史观点来看,梁无疑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来自外来帝国主义这一显然的事实,而且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只有以反帝为目标,才能使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灵活地抵挡住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称的“整合革命”;整合革命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与民族主义的出现同时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民族意识的觉醒,就像后来发生的民族分离以及由各种原始忠诚哺育起来的离心趋势一样,使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国家陷于分裂的危险。反满自然是这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暂时可作为政治上一个可资利用的战斗口号,但它肯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长远目标背道而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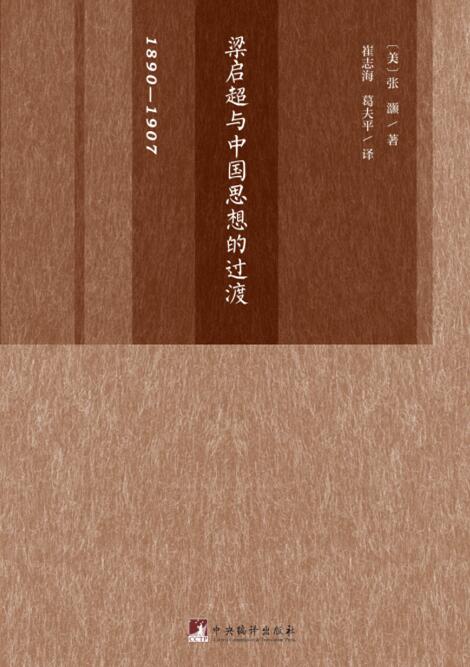
[美] 张灏 著
崔志海 葛夫平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6月



















